
范申,大丰白驹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工商银行盐城大丰支行工作人员。作者自幼生活在白驹,对古镇白驹有着深厚的故乡情感。近年来作者创作了20多篇白驹风土人情的散文,入选《乡愁若灯》《魅力大丰》等书籍,并发表在国内多家报刊杂志。白驹是作者的心灵港湾、是作者的写作源泉,更是作者每每回望故乡时,充盈在心间的满满乡愁。

我的青年时代。
1687年的初春,海风寒冽,一艘高大宽阔的木制官船,在尚未散尽的薄雾中向古镇白驹北闸的一处码头靠近。正在海边捕鱼劳作的渔民们被一阵鞭炮声惊起,抬眼望去,两列锦衣华冠的队伍正在码头接候着走下官船的几位人员。原来,这是白驹场署大使王国佐和草堰场署大使钟铎率领两场官员,恭迎工部侍郎孙在丰和国子监博士孔尚任。两位当朝钦差是奉康熙皇帝的御旨到白驹、西团一线督察东洋海口水利治理工程来了。
见礼寒喧之后,工部侍郎孙在丰和国子监博士孔尚任便移步来到了白驹场河岸边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旁,随行的白驹场署大使王国佐向前一指:“两位大人,前面就是白驹场的北大街,下官恭请大人们前去察看市井街况!” 于是,一行人员在王国佐的带领之下,来到了白驹场区中心的北大街。
白驹,串场河边的一座因盐而起的古镇,始建于元代中后期,称为“白驹场”,隶属泰州府海陵监管辖,是名盛两淮的重要盐场之一。在白驹场,存放盐包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为了人们的聚集之所,北大街的雏形渐渐形成。
是日,当王国佐引领一行人员来到北大街的时候,麻石铺就的大街两侧,暮霭之中的老屋民宅炊烟正起,数十步之外的几家店铺已经灯火闪烁,古镇的晚市还没有打烊,整肃清朗的街区流连着暖暖的家常气息……眼看天色向晚,明天还要东行三十里河,工部侍郎孙在丰说道:“时间紧迫,我们赶紧在此休息吧!”
当夜,在白驹歇息的馆舍内,青灯摇曳之下的一张书桌前,孔子第64代孙、在御前讲述《论语》深得康熙皇帝褒奖的孔尚任感慨万千。海边白驹的景色风光让他触景生情,他立即展开一张纸,管毫飞舞之间,一首五言绝句《宿白驹场》一挥而就:海雾暮皆连,海风春更急。维舟在白驹,聊以永今夕。
时光过去了330年,如今在古镇白驹的街巷和课堂之上,这首诗作仍在被朗读传诵,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2001年出版的高中选修课本《江苏风情》中,该诗是唯一入选代表盐城风土人情的诗作。
我的故乡在白驹,老家就在古老沧桑的北大街,从小时候我便喜爱这首《宿白驹场》。古镇充满人文风华,清幽而厚重,是我成长的摇篮,如今这里老墙斑驳,宅院深深,古巷幽幽,那些穿过时空隧道的时光碎影,仍在这里辗转吟唱。
北大街是一条蜿蜒曲折、数百米长、东西走向、只数米宽的老街,这里有我童年欢快的笑语、少年春天里的呼吸和青年惆怅起的沉思。如今,人到中年的我每每走过北大街,心情沉静而平缓,那些铺街而过的麻石、灰砖墙上深深浅浅的苔痕、青檐上摇曳的荒草、在风雨中有些飘摇的老宅,无不在向我诉说着它们的饱经风霜和如烟岁月。行走在北大街上,我就如同面对一位沧桑的老者,带着对逝去年华的忆念,我们一次次地回首和追想。
北大街多为白驹五大姓氏陈、杨、李、施、卞中的杨姓、施姓人家世代居住。公元1353年,古镇的南首界牌头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一个叫张士诚的盐民在一座破庙里揭竿而起,十八条盐民的扁担演绎了一段风风火火的硝烟故事,张士诚继而还在苏州称了王。这其间,白驹一位当朝进士施耐庵在追随张士诚后,因谋事不合弃军而去、一路辗转后又回到了白驹场,在花家垛上设馆教徒、著书立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那些流水寻常的日子里,人们都可以在北大街的青砖小径上看到耐庵先生或驻足思索,或探访市民,一个个的民间故事被先生仔细揣摩,那些生动传神的乡间俚语也被先生一一记在心里,谈笑交流之间先生“替天行道、革故鼎新”思想在酝酿升华,他虽身在河网之中的白驹小镇,然而胸中有丘壑,腕底起云烟,最终在这里成就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这是一个人的奇迹,也是白驹的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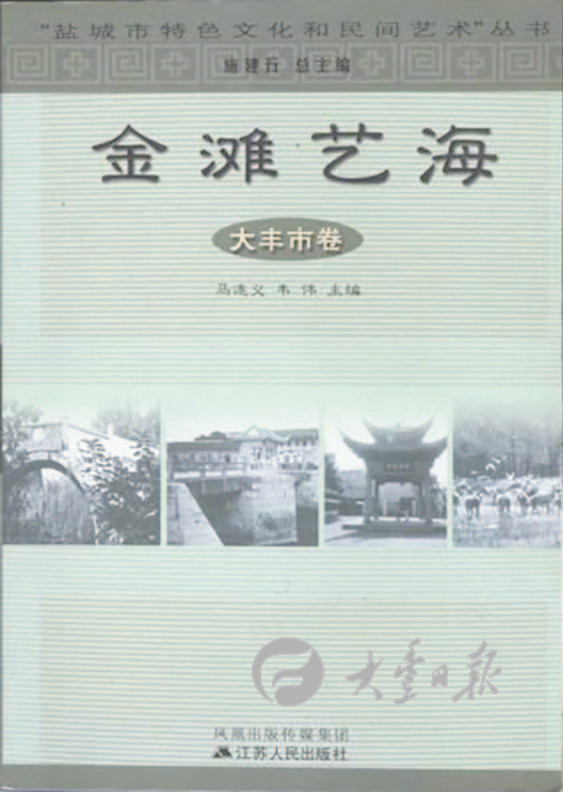
记载白驹特色文化的地方文史资料。
耐庵先生的才思文华在北大街写下了几多清新婉约的诗词歌赋,同时用北大街的市井风情刻画了许多非凡的经典故事。而平凡普通的北大街又寄托过先生多少家国情怀,引发过先生多少人生思考?我想,抚过北大街的那缕轻风知道,飘过北大街施氏宗祠遗址上的那朵祥云知道,来过北大街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

北大街现景。
北大街是一条平民的街,这里虽然没有宰相府、状元第或是御史巷,但北大街同样有着丰富的历史文明和人文风华,先贤士人同样在此留下了印迹。最古老的一处胜迹当数佑圣观。据传该观始建于唐代,庙宇的规模并不大,其西侧有一处小殿,供奉有汉代神医华陀的塑像,后来这座小殿也就成了白驹一带颇有名气的“东药王庙”。几经战乱和动乱,佑圣观早已不复存在,只在白驹北大街一个小巷内,如今还保留了一处人们敬奉华陀的华陀庙。说是庙,其实只是一处不大的普通房子,这里延续着白驹人民尊医向善、祈求健康的淳朴民风。
在北大街,白驹的后人为景仰当年范仲淹筑堤护民之功,在这里修建了三贤祠,祠内供奉有文正公范仲淹、文定公胡令仪、文襄公张伦的神牌。公元1704年,人们又在三贤祠内建起了诚意书院,白驹的文脉书香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到了民国时期,诚意书院又演变而成了白驹小学的北学堂,北大街的文风之气蔚然而续。
白驹因盐而起,曾有过商铺云集、帆樯林立、舟车络绎的盛况。商业繁荣,财富激增,人们向往着“氤氲一脉心香、宁静而能致远”的禅意生活,白驹陆续建起了东岳庙、关帝庙等数座规模宏大的庙宇。

居氏酱园。
如今在北大街上经营熏烧卤菜的“王老九卤菜店”店主王荣贵是土生土长的北大街人,今年已经68岁。王荣贵听他的父亲说,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街最是热闹。北大街的东西首还曾建有高大的门楼:东圈门和西圈门,人们在远处早早就能看到这两处标志性建筑。那时,沿着北大街行走,店坊商铺比肩接踵,一家连着一家,客栈、浴室、剃头店、茶食店,烟酒店、豆腐店、南货店,洋货店、酱园、茶炉、炕坊……那时的王家经营着一家“天生饭店”,每天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如今王荣贵子承父业,并将一套卤制手艺传给了他的女儿。他们秘制的猪头肉、皮卷、豆汁干等通过互联网将饱含白驹北大街的乡土风味送到了深圳、澳门、北京、长沙等地,家乡的游子们尝一口地道的熏烧卤菜,总会在心中忆起那份淡淡的乡愁。
北大街曾是古镇的生活中心,如今这条古老的大街边还留有百年老店喻家茶食作坊的旧址。喻永楠,今年64岁,自幼在北大街成长,他家几代人都曾专做茶食生意,是白驹北大街有名的旺户。说起喻家茶食店和北大街的往事,喻永楠透露,茶食店除了生产馓子、脆饼、金刚脐、麻切、果子等传统茶食外,一年四季还生产不少应时食品。春天的时候做些油端子、藕夹子;夏季时生产八珍糕、薄荷糕;中秋时生产月饼;过年时生产寸金糖、芝麻糖、花生糖等。喻家茶食原料地道、做功精细、品质上乘,绝不使用防腐剂和添加剂,因而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喻永楠说,白驹人喜欢看戏,那时晚上从戏园子散戏归,再来到喻家茶食店品尝一下蟹粉包子实在是一大享受。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合作化生产后,喻家茶食这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老白驹人几个时代的味蕾记忆。
漫步北大街,两边的小巷子是一条挨着一条。小巷不是统称的巷子,而是一条位于北大街街南的一条巷子的名字。在小巷之西,又有一条较为宽些的巷子,白驹人称为大巷。一条条的巷子深深浅浅,它们一起连结起了北大街的前尘往事和不灭记忆。从北大街的东首步行约百米,有一条巷子称为太平巷,旧时巷内的人家也是青砖小院,古意盎然。
据史载,明朝之初,白驹场的东面就是浩瀚的南黄海,时常有倭寇来白驹场出没骚扰。白驹场的民众奋起抗争,数场激烈的战斗后消灭了不少来犯的倭寇,这些倭寇的尸体就被掩埋于如今的太平巷一带,太平巷名称的由来也是寄寓了人们企望太平和安稳的意愿。在白驹北大街的店桥口还有一处当时人们掩埋倭寇尸体的地方,即如今的白驹倭子桥遗址所在。硝烟的故事已经远去,但白驹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北大街的光辉岁月里。
在北大街,这里曾经还有一处救助孤儿、弃儿的“存仁堂”。白驹解放前,为了收留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几位开明人士慷慨解囊,建起一处只有三间房屋的民间收容所——存仁堂。他们雇请了专门人员负责孩子们的起居生活,在那个苦难的社会里为这些不幸的孩子撑起了一方关爱保护的天空,北大街由此更多地洋溢起仁爱和温暖,古镇白驹的德行善品在这里发扬光大。据了解,这块写有“存仁堂”三个字的石板至今仍保存在北大街一户陈姓人家里。

施耐庵故居遗址。
时光是无情的演绎大师,如今,许多古意盎然的庙宇、店铺和宅院在北大街已都不存在了,但北大街仍然保留了白驹最原始的根脉。街边旧宅上的鱼鳞瓦里瓦楞花依旧颤巍巍地摇摆,小院里的青石老井静静地卧在了一抹清寂之中,老屋檐下的香炉里一缕轻烟正袅袅地弥散飘忽……
老街无语,古巷沉默,小院幽深,所有的辉煌与风流一任风吹雨打而去,只有这里那些遒劲的老树、低矮的门脸、古朴的花窗仍在展示着北大街固有的气度和韵味。旧时的铺街石板还在,沿街的浴室、茶炉等又重新开张了起来,堂子巷里老浴客们仍是喜欢着这里晚上水包皮的惬意,老店的卤菜还是熟悉的白驹味道,卖早茶的小店里冒着热气……时间已经沉淀为历史,在北大街的慢时光里一切依稀如昨。
细碎的阳光从杨家巷的一处庭院里洒过,那棵饱经沧桑、枝叶婆娑的古银杏满树翠绿。归来的燕子又在老屋的檐下开始了啁啾,那只老猫还是乖乖地蹲坐在街角巷口,街边门前的月季花依旧散发出淡淡馨香。北大街从容地一步步走来,送走了柔美的月亮,又迎来了初升的朝阳,沐浴着雨雪风霜,穿过了历史烟云,它带着白驹的岁月坐标和文化密码,已经永远地辉映在了古镇白驹的韶光和华美之中。

老理发店。

我的祖母杨茂先与父亲范国夫在老屋前合影。


